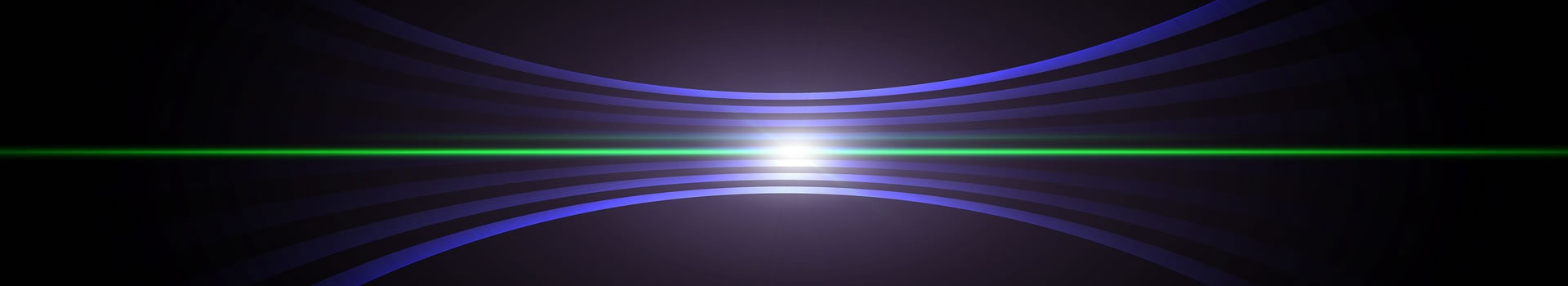

声明:本篇故事为虚构内容,如有雷同纯属巧合,采用文学创作手法有粘钢绞线,融合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元素。
故事中的人物对话、情节发展均为虚构创作,不代表真实历史事件。
帐外的风像狼嚎。
他走进来,带着一身酒气和寒意。帐篷的帘子被猛地放下,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喧闹。
“从今天起,你就是我的阏氏。”复株累的声音沙哑,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王昭君坐在铺着新羊皮的床边,一动不动,仿佛没听见。
“我父亲的女人,现在归我了。”复株累的耐心在消失,他上前一步,“这是草原的规矩。”
王昭君猛地抬头,那双眼睛里没有泪水,只有刺骨的冰冷:“规矩?逼迫一个名义上的母亲,也是规矩吗?”
“放肆!”复株累大怒,一把抓住她的手腕,“王昭君,别考验我的忍耐!”
她的手腕被捏得生疼,但她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。
王昭君直视着他,在窒息的沉默中,一字一句地开口:“单于若想让我顺从,就必须答应我一个请求。”
01
边关的烽火台已经有十年没有点燃过了。牧民们几乎忘了狼烟是什么味道。
可是今天黄昏,那股夹杂着草木灰和焦臭的风,还是吹进了匈奴的王庭。这不是汉朝的军队打来了,而是匈奴的天塌了。
老单于呼韩邪,死了。
他死得很突然,中午还喝了一大碗羊奶,说要去看看新生的马驹。下午,人就倒在了马厩里,再也没起来。
整个王庭瞬间炸开了锅。女人们的哭嚎声,男人们的喊叫声,混成一团。萨满的鼓声咚咚地敲了起来,急促得像是要催走所有活人的魂。
王昭君麻木地坐在大帐的角落里。
她的帐篷是王庭里最华丽的,地上铺着汉朝来的丝绸毯子。但现在,她只觉得冷。
她没有哭。呼韩邪对她很好,像一个长辈,给了她十年的安稳和庇护。但那不是爱,而是一种客气。她对他,有感激,有尊敬,但没有男女之情。
所以,她不悲伤。
她是恐惧。
她紧紧抓着自己幼子伊屠智牙师的手。孩子才八岁,吓得缩在她怀里,不敢出声。
王昭君很清楚,老单于一死,她这个汉朝来的阏氏,就像是草原上失去了牧人看管的羊,瞬间会引来无数双狼的眼睛。她的庇护伞,没了。
帐篷的帘子被人粗暴地掀开,一股寒风灌了进来。
一个人高马大的身影走了进来,他身上的皮甲还带着外面的寒气。
王昭君的心猛地一缩。
是复株累。呼韩邪的长子。
他现在是新单于了。
复株累是个沉默的男人,脸庞像刀削一样硬朗。他才三十出头,正是狼一样强壮的年纪。
这些年,他很少和王昭君说话。但王昭君总能感觉到他的目光。那是一种和老单于完全不同的目光,不带敬意,不带客气,而是带着一种原始的、滚烫的、想要占有的东西。
现在,老单于死了,他成了这片草原的主人。
他继承了呼韩邪的王位、部众、牛羊,以及……他父亲所有的女人。
复株累的视线穿过帐篷里混乱的人群,越过那些哭天抢地的匈奴女眷,像钉子一样,牢牢钉在王昭君的脸上。
他的眼神像草原的冬夜,冰冷,又深得看不见底。
他就那样隔着人群,静静地注视着她。
王昭君抓着儿子的手,指甲都快掐进肉里。她知道,她的安稳日子到头了。
02
老单于的葬礼持续了三天三夜。
匈奴人的葬礼,没有汉朝那么多的繁文缛节,但充满了原始的悲怆和敬畏。
王昭君作为呼韩邪的阏氏,被迫穿上粗麻的丧服,跟在送葬的队伍里。她的头发被弄得乱糟糟的,脸上也被抹上了炉灰。
她像一个木偶,任由那些匈奴的老阿妈摆布。
在下葬的最后仪式上,部落的大萨满出场了。
他戴着狰狞的青铜面具,身上挂满了骨头和羽毛,在火堆旁疯狂地跳着舞。他的嘴里念念有词,声音沙哑得像两块石头在摩擦。
鼓声越来越急。
突然,萨满猛地停了下来,用骨杖指向天空,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嚎。
所有人都跪了下去,连复株累也低下了头。
萨满开始宣告神谕。
他说:“老单于的灵魂不愿离去,因为他还有最珍爱的宝物留在了人间。这件宝物,是草原的明珠,是汉朝送来的和平信物。如果这件宝物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,老单于的灵魂将不得安息,草原将会降下灾祸。”
王昭君跪在地上,浑身冰冷。
她听懂了。那个“宝物”,指的就是她。
这不是什么神谕,这是逼迫。这是在用神灵的名义,来掩盖一个野蛮的习俗。
葬礼一结束,部落里最有威望的几个老阏氏——她们都是前几代单于的遗孀——就走进了王昭君的帐篷。
她们的脸上布满了皱纹,像干裂的土地。
“阏氏,”为首的老阿妈开口了,声音很硬,“萨满的话,你听到了。”
王昭君低着头,没有作声。
“按照我们匈奴的规矩,”另一个老阿妈接着说,“父亲死了,他的儿子,就要娶他的后母。这样,家族的血脉和财产才不会外流。”
“这,是为了部落的强大。”
“你虽然是汉人,但你嫁给了单于,就是我们匈奴的女人。你必须遵守这里的规矩。”
她们的话,一个字一个字,像冰雹一样砸在王昭君的心上。
她当然知道这个规矩。在汉朝,这叫“乱伦”,是禽兽才做得出的事情。
她这十年来,一直刻意回避去想这件事。她总以为呼韩邪会长命百岁,她总以为自己能平安地把儿子养大。
可现在,这个最让她恐惧的事情,还是来了。
“不……”她用尽全身力气,才从喉咙里挤出这个字,“我是你们新单于的……母亲。”
“你不是他的生母。”老阿妈冷冷地打断了她,“你只比他大几岁。在草原上,只有强者才能保护女人。老单于去了,现在复株累单于是新的强者。你就应该归他所有。”
“这也是为了你好。”另一个老阿妈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,“你一个外族女人,带着个孩子。没有新单于的庇护,你们母子俩,活不过这个冬天。”
老阿妈们走了。
王昭君坐在冰冷的地毯上,许久许久,一动不动。
03
王昭君病了。
或者说,她假装自己病了。
她以需要为老单于守丧、身体虚弱为由,拒绝了新单于复株累召见她的一切要求。她闭门不出,每天只让侍女送一点点食物。
她需要时间。
她不能坐以待毙。
夜深人静时,王昭君悄悄喊来了那个从长安一直跟着她的老侍女。
“玉姑,”她压低声音,“我们还有多少金子?”
“阏氏,我们出塞时带的赏赐,老单于这十年又给了不少,都还在。”
“你去找找,”王昭君的眼睛在黑暗中发亮,“找到当年护送我们来的那几个汉朝侍卫。他们应该还在王庭。你告诉他们,谁能把我带回长安,这些金子,全归他。”
玉姑吓得跪在地上:“阏氏,这……这是逃跑啊!被抓住了,我们和孩子都活不了!”
“不试试,我们连这个冬天都活不过去!”王昭君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,“复株累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必须走。”
玉姑抹着眼泪,领命出去了。
接下来的两天,王昭君都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。
然而,玉姑带回来的消息,让她坠入了冰窖。
那几个汉朝侍卫,有的,已经在十年的风沙中病死了。有的,娶了匈奴女人,生了孩子,彻底成了牧民,根本不敢再回汉朝。
还有一个,前天晚上,喝醉了酒,掉进河里淹死了。
太巧了。
王昭君瞬间明白了。她的所有举动,都在复株累的监视之下。那个淹死的侍卫,恐怕根本不是意外。
复株累是在用这种方式警告她,她插翅难飞。
这天深夜,王昭君怎么也睡不着。
忽然,帐篷的帘子被轻轻掀开,一个高大的黑影走了进来。
王昭君吓得坐了起来,抓紧了身边的剪刀。
“是我。”
是复株累的声音。
他没有穿戴单于的金饰,只穿着一身最普通的牧民皮袍。他身上没有酒气,只有一股浓重的寒气。
他点燃了帐篷里的油灯。
豆大的火光,照亮了他那张轮廓分明的脸。
他没有靠近,只是站在帐篷中央,看着王昭君。
“你病了?”他先开口。
“……是。多谢单于关心。”王昭君握着剪刀的手心全是汗。
“我看你气色还好。”复株累淡淡地说。
帐篷里陷入了可怕的寂静。只有外面的风声在呼啸。
“我今天,”复株累忽然开口,换了半生不熟的汉语,“去看了父亲的马。那些马,现在都是我的了。”
王昭君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“父亲的帐篷,也是我的了。”他往前走了一步。
王昭君往后缩了缩。
“王昭君,”他盯着她的眼睛,“你来草原十年了。”
“……是。”
“你觉得,”他慢慢地问,“是长安的月亮圆,还是我们草原的月亮圆?”
这是一个陷阱,一个试探。
王昭君的后背已经湿透了。她知道,她的回答,将决定她和儿子的命运。
她如果说长安的月亮圆,那她就是心向汉朝,他有足够的理由处置她。
如果她说草原的月亮圆,那她就是归顺,必须接受他的安排。
王昭君深吸了一口气,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“单于,”她缓缓开口,声音尽量平稳,“月亮,本没有分别。它照在长安的宫殿上,也照在草原的帐篷上。它照着汉人,也照着匈奴人。”
复株累的眼睛眯了起来。
他没想到,这个一向温顺的汉朝女人,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他盯了她很久,久到王昭君几乎要窒息。
“你很聪明。”他冷冷地丢下三个字。
“好好养病。三天后,就是我们大婚的日子。”
说完,他转身,掀开帘子,消失在夜色中。
王昭君浑身脱力有粘钢绞线,瘫倒在毯子上。她知道,她最后的退路,被堵死了。
04
复株累走了。
但王昭君帐篷外的守卫,从两个,变成了十个。
这些士兵,她一个都不认识。他们是复株累的亲兵,年轻,精壮,眼神像狼一样警惕。他们只听新单于的命令。
王昭君彻底成了一个囚犯。
玉姑哭着说:“阏氏,怎么办?三天后……我们怎么办啊?”
怎么办?
王昭君也在问自己。
她试过用金钱收买,失败了。她试过用言语拖延,也被看穿了。
她写了信,一封给长安的皇帝,一封给她的家人。她求玉姑无论如何想办法送出去。
可是,玉姑才走出帐篷,就被守卫拦下。信被搜走,当着她的面,扔进了火盆。
绝望,像草原的冬天一样,瞬间席卷了她。
她没有路了。
嫁给复株累?那个她名义上的儿子?那个眼神灼热的男人?
她只要一想到那个画面,就恶心得想吐。汉朝的礼教,像一条绳索,死死勒着她的脖子。她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。
死。
这个念头,像一颗毒草,疯狂地在她心里生长。
死了,就一了百了。
没有屈辱,没有折磨。她还是那个为国和亲的汉朝臣子,她守住了自己的清白。
夜里,她支开了玉姑。
王昭君从妆匣的暗格里,拿出了一把小巧的玉柄剪刀。这是她当年离开长安时,母亲塞给她的。
她握着冰冷的剪刀,对准了自己的脖子。
她想起了长安的柳絮,想起了阿妈做的桂花糕。她想,她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就在王昭君闭上眼睛,准备用力刺下去的时候——
“阿妈!”
帐篷帘子被掀开一条小缝,她八岁的儿子伊屠智牙师钻了进来。
孩子显然是刚睡醒,揉着眼睛,光着脚丫。
“阿妈,我冷。”
王昭君手一抖,剪刀掉在了地毯上,发出了沉闷的声响。
她赶紧把剪刀踢到毯子下面。
孩子扑进了她怀里,小小的身体还在发抖。
“阿妈,”他仰着黑亮的眼睛,小声问,“我听外面的叔叔说,阿爸死了。他们还说……还说我们要有新阿爸了。”
孩子的童言无忌,像一把钝刀,剜着王昭君的心。
“阿妈,”他抱紧了王昭君的脖子,声音里带着哭腔,“我们以后,是不是没有家了?”
“轰”的一声。
王昭君的脑子炸开了。
她看着怀里这个流着一半汉人血统、一半匈奴血统的孩子。
她死了,是解脱了。
可儿子怎么办?
他才八岁。在这片弱肉强食的草原上,没有了她的庇护,复株累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们,会把他撕得粉碎。
他会被当成奴隶,被流放,甚至被杀死。
王昭君猛地抱紧了儿子。
不。
她不能死。
为了儿子,她必须活着。
哪怕是像狗一样,屈辱地活着。
王昭君放下了剪刀。但她的心,比握着剪刀时还要冷。
她不能只是“活着”。她要让她的儿子,也好好地活着。
她开始冷静地思考。
复株累为什么一定要娶她?
因为匈奴的规矩?是,这是一部分。
更重要的是,他刚刚即位,王位不稳。他需要她这个“汉朝阏氏”的身份,来向汉朝示好,表示和平会继续。他也需要她这个“老单于遗孀”的身份,来安抚呼韩邪的旧部。
她,王昭君,是一个政治筹码。
既然是筹码,那就有谈判的价值。
王昭君的眼睛,在黑暗中,慢慢地亮了起来。她不再是一个绝望的女人,她是一个要保护幼崽的母亲。
她不准备逃了,也不准备死了。
王昭君准备,和新单于谈一笔交易。
05
手机号码:13302071130三天的时间,一晃而过。
婚礼的日子到了。
整个匈奴王庭都沸腾了。这不仅是新单于的婚礼,更是他巩固权力的宣告。
牧民们杀牛宰羊,大块的烤肉在篝火上滋滋作响,浓烈的马奶酒香气飘出了几十里地。
男人们围着火堆跳舞,放声高歌。
这一切的喧闹和喜庆,都和王昭君的帐篷无关。
她的帐篷里,冷得像冰窖。
几个匈奴的老阿妈走了进来,她们手里捧着一套大红色的嫁衣。
那是匈奴款式的皮袍,钢绞线厂家用最上等的汉朝丝绸缝制,上面用金线绣着草原的飞鹰和奔狼。
“阏氏,请更衣。”老阿妈的语气,不带任何感情。
王昭君像个木偶一样,任由她们扒下自己的丧服,换上那身刺眼的红装。
衣服很重,上面镶嵌的宝石和金饰硌得她皮肤生疼。
她们又给她戴上了沉重的黄金头冠,坠得她几乎抬不起头。
“阏氏,您真美。”一个年轻点的侍女讨好地说。
王昭君看着铜镜里那个人。
一张苍白到没有血色的脸,一双空洞到没有焦距的眼。
这张脸,既熟悉,又陌生。
她还是王昭君吗?还是那个长安城里弹着琵琶、梦想着爱情的少女吗?
她不知道。
王昭君只知道,她是一个准备上战场的士兵。
帐外的喧闹声,像潮水一样,一阵阵拍打着她的耳膜。马头琴的声音,男人的呼哨声,女人的嬉笑声。
她什么都听不见。
夜,渐渐深了。
外面的声音小了一些。狂欢的牧民们,大概都喝醉了。
时间一点点流逝。
王昭君就那么坐着,一动不动。
忽然,帐篷的帘子,被一只强壮有力的手,猛地掀开了。
复株累走了进来。
他喝了很多酒,脸颊通红,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,亮得吓人。
他也穿着一身红色的新郎袍子,腰间挂着金鞘的弯刀。他高大的身影,几乎挡住了帐篷的入口。
“你们都下去。”他挥了挥手。
帐篷里的侍女和老阿妈们,如蒙大赦,慌忙退了出去。
帘子落下。
整个世界,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
帐篷里很安静,只有牛油大烛燃烧时,发出的“噼啪”声。
复株累一步一步朝她走来。
他身上浓烈的酒气,混合着男人的汗味和皮革味,扑面而来。
王昭君感到了强烈的窒息。
他站定在她面前,低头看着她。
“你……”他开口,声音有些沙哑,“你今天,很美。”
王昭君没有抬头,也没有说话。她只是死死地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。那双手,十指交叉,握得指节都发白了。
“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。”复株累又说,“但是,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我也是为了部落,为了大家。”
他试图解释。这个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的男人,此刻,竟然显得有些笨拙。
“你放心,以后,我会像父亲一样……不,我会比父亲对你更好。”
王昭君依旧一动不动,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。
复株累的耐心,似乎被耗尽了。
他的脸色沉了下来。帐篷里的气氛,瞬间降到了冰点。
“王昭君。”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她,语气里带着一丝恼怒,“你现在是我的阏氏。你最好搞清楚这一点。”
他上前一步,伸手想去扶她的肩膀。
“别碰我!”
王昭君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,猛地一颤,厉声说道。
复株累的手,僵在了半空中。
06
帐篷里的空气,仿佛在瞬间凝固了。
复株累的手还停在半空,他的脸色铁青。作为新单于,他还从没有被一个女人这样当面顶撞过。
他握紧了拳头,骨节“咔咔”作响。
他以为她会哭,会闹,会像别的女人一样哀求。
可王昭君没有。
她只是猛地抬起头,直视着他。
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。
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和绝望,也没有泪水。那双眼睛,像塞北冬天的湖面,结了厚厚的一层冰,冰冷,平静,又深不见底。
复株累被她看得一愣。
他从没见过这样的王昭君。
以前,她总是低着头,温顺,沉默,像一件精美的瓷器。
而现在,她像一把出了鞘的刀。
“你再说一遍?”复株累的声音里带着威胁。
王昭君没有理会他的威胁。
她看着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、名义上却是她“继子”的男人。她知道,这是她唯一的机会。
“单于。”
她平静地开口了,声音不大,甚至有些虚弱,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“你娶我,不是因为你喜欢我。你需要我。”
复株累累眯起了眼睛。
“你需要我这个‘汉朝阏氏’的身份,去稳住汉朝,让他们继续承认你的王位,继续和你们通商。”
“你需要我这个‘呼韩邪阏氏’的身份,去安抚那些还念着老单于旧情的部落首领。”
“你需要我的儿子伊屠智牙师,因为他身上流着呼韩邪的血,也流着汉朝的血。他活着,就能证明你是宽容的,是正统的。”
王昭君的每一句话,都像一把小锤子,准确地敲打在复株累的心上。
复株累的表情,从愤怒,变成了错愕,最后变成了凝重。
他收回了手,后退一步,重新审视着眼前这个女人。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?”
“我想说,”王昭君深吸一口气,“我可以配合你。我可以当你的阏氏,我可以帮你安抚部落,我也可以写信给汉朝皇帝,说我过得很好,让他册封你。”
复株累的眼神亮了。这正是他最需要的。
“但是。”王昭君话锋一转。
“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请求。”
“什么请求?”复株累沉声问。他知道,这个女人的请求,绝不简单。
王昭君站了起来。
她身上的黄金头冠太重了,她索性一把摘下来,扔在地上,发出了“哐当”一声巨响。
她直视着复株累的眼睛,一字一句地说:
“第一,你要以匈奴狼神的名义,也要以汉朝宗庙的名义,共同立下血誓——在我王昭君有生之年,匈奴铁骑,绝不主动南下一步,踏入汉朝边关!”
复株累的瞳孔猛地一缩。
“第二,”王昭君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,继续说道,“你必须马上册封我的儿子,伊屠智牙师,为匈奴的‘左贤王’!”
“左贤王”是匈奴语里“最贤能的王”的意思,地位仅次于大单于,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。
“并且,”王昭君加重了语气,“你要用汉朝的礼仪来册封他!你要上书汉成帝,请求汉朝皇帝,也同时承认我儿子的储君地位!”
帐篷里,死一样的寂静。
复株累被王昭君这番话,震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
07
复株累怎么也没想到,这个看似柔弱的汉朝女人,会在这个晚上,向他提出如此大胆、如此精准的政治条件。
这不是一个女人的哀求。
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谈判。
她用她自己,和她儿子的未来,作为筹码,一头连着汉匈的和平,另一头,连着匈奴内部的储君之位。
复株累的酒意,瞬间全醒了。
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,死死地盯着王昭君。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”他的声音里透着危险,“你是在威胁我?”
“我不是在威胁你,单于。”王昭君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,“我是在帮你。”
“帮我?”复株累冷笑一声。
“是。”王昭君说,“你刚刚即位,你的几个兄弟都盯着你的王位。部落里,那些老单于的旧部,也未必真心服你。你为什么急着娶我?不就是为了稳住局面吗?”
“你答应我第一个条件,”王昭君开始分析,“汉匈和平。汉朝皇帝高兴了,就会给你更多的赏赐和贸易。边关的牧民不用打仗,就能换来粮食和铁器。你的子民会拥护你。”
“你答应我第二个条件,”她的声音更稳了,“册封我儿子为左贤王,还是用汉朝的礼仪。这等于向所有人宣布,你得到了汉朝的全力支持。你那些想造反的兄弟,还敢动吗?那些摇摆不定的老臣,还敢不服你吗?”
复株累在帐篷里来回踱步,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。
他不得不承认,这个女人说的,全对。
她看透了匈奴的局势,也看透了他这个新单于最大的焦虑。
他需要和平,需要稳定。
而王昭君,把这两样东西,打包送到了他面前。
代价是,他必须发誓,并且把未来的王位,交给一个流着一半汉人血统的孩子。
复株累停下脚步。
他看着王昭君。这个女人,在刚才短短的几句话里,已经彻底变了一个人。
她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“阏氏”,她是他政治上的对手,或者说……盟友。
“如果我不答应呢?”他做了最后一次试探。
王昭君惨然一笑。
她弯腰,从地毯下,捡起了那把玉柄剪刀后,把剪刀横在自己雪白的脖颈上。
“单于,”她轻声说,“你如果非要一个屈服的奴隶,那你今晚得到的,只会是一具尸体。”
“一个自尽的汉朝阏氏,一个刚刚即位就逼死先父女人的新单于……你猜,汉朝皇帝会怎么想?草原上的牧民,又会怎么想?”
复株累的拳头,握得死紧。
他知道,他输了。
输给了这个他本以为可以随意摆布的女人。
“好。”
过了很久,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。
“我答应你。”
他看着王昭君,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答应你的全部请求。”
王昭君握着剪刀的手,在轻微地发抖。但她的表情,依旧平静。
“口说无凭,我要你立誓。”
复株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。
他拔出腰间的弯刀,划破了自己的手掌。
“我,复株累,”他举起流血的手,“以匈奴狼神和汉朝宗庙的名义起誓。在王昭君有生之年,绝不主动南侵!我愿册封伊屠智牙师为左贤王,并请求汉帝共同册封!”
王昭君看着他。
她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剪刀。
“好。”她说,“从今天起,我就是你的阏氏。”
这一夜,大帐的红烛烧到了天明。
但他们两人,一个坐在床边,一个坐在桌案旁,一夜未眠。
他们谈论的,不是风月,而是汉匈的边境贸易、部落的派系,以及如何安抚那些手握重兵的部族首领。
天亮时,复株累走出帐篷。他没有得到一个温顺的妻子,但他得到了一个最清醒、最强大的政治盟友。
08
那晚的谈判,彻底改变了王昭君的命运,也改变了匈奴的走向。
复株累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君主。
三天后,他便召集了所有部落首领,当众宣布册封伊屠智牙师为左贤王。同时,他派出了最隆重的使团,前往长安,向汉成帝上书,请求汉朝的共同册封,并重申了和平的誓言。
汉成帝收到了复株累的国书,又读了王昭君的“家书”——信中,王昭君用平静的语气,叙述了自己对汉匈和平的信念,以及新单于对汉朝的“仰慕”。
汉成帝龙颜大悦。
他立刻派使者回访,带去了丰厚的赏赐,并正式承认了复株累的单于之位,以及伊屠智牙师的储君地位。
复株累的王位,瞬间稳如泰山。
而王昭君,她的身份也彻底变了。
Skip表示:“显然文班不喜欢霍姆格伦(不管什么原因),他喜欢击败并压制切特(霍姆格伦),用切特面对其他人时不会感到畏惧的方式来恐吓他。面对文班,霍姆格伦畏缩了,确实如此,文班在心理和身体上都吃定了他。”
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男人生存的阏氏。她成了匈奴的“国师”,成了复株累最信任的政治导师。
复株累名义上是她的丈夫,但在内心里,他对这个女人充满了敬畏。他下令,王昭君的帐篷,任何人不得允许,不准擅入,包括他自己。
王昭君没有成为复株累真正意义上的妻子,她把所有的精力,都放在了两件事上。
第一,她用汉朝的文化和政治手腕,帮助复株累平衡部落内部的各个派系。她教他如何用贸易来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小部落,如何用汉朝的律法来约束部下。
第二,她全力教导她的儿子,伊屠智牙师。
她不仅教他匈奴的骑马射箭,更教他汉朝的兵法和《春秋》。她要让他明白,一个真正的王者,靠的不是蛮力,而是智慧。
伊屠智牙师在母亲的教导下,成长得非常出色。他既有匈奴人的勇猛,又有汉朝人的儒雅和谋略,深得两族人民的爱戴。
在王昭君的斡旋下,她立誓的那些年里,汉匈之间真的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。
边关的烽火台,再也没有点燃过。
商旅的驼铃声,取代了战马的嘶鸣。丝绸、茶叶和铁器,源源不断地流入草原;而骏马、皮毛和牛羊,也丰富了汉朝的市场。
时光飞逝。
几十年过去了。
王昭君老了。她的头发全白了,脸上的皱纹,像极了当年她见过的那些老阿妈。
她快要死了。
复株累也老了,他已经是一个威严的老单于。她的儿子伊屠智牙师,也已经人到中年,成为了众望所归的继承人。
在王昭君生命的最后一刻,复株累和伊屠智牙师都守在她的床边。
“母亲……”伊屠智牙师握着她的手,泪流满面。
王昭君缓缓睁开眼,她看向了复株累。
“单于,”她的声音,像风中的残烛,“我还有一个请求。”
“你说。”复株累的眼眶也红了。这几十年来,他从这个女人身上学到的,比从他父亲身上学到的还要多。
“我死后,”王昭君轻声说,“请把我……和呼韩邪单于合葬在一起。”
复株累和伊屠智牙师都愣住了。
这是她最后的坚持。
王昭君承认复株累是盟友,是君主,但她不承认他是她的丈夫。她死,还是要回到那个最初给她十年庇护的、老单于的身边。
那是她作为汉朝臣子,最初的归宿。
复株累沉默了很久。
他最终点了点头:“好。我答应你。”
王昭君笑了。她这一生,从长安到塞外,从绝望到抗争,她守住了她的儿子,也守住了两个民族的和平。
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
复株累也按照她的遗愿,将她与呼韩邪合葬。
在她的陵墓前,复株累下令,点燃了一盏灯。
那盏灯,是当年汉成帝赏赐给王昭君的,一盏来自汉朝皇宫的“长乐”宫灯。
复株累下令:“这盏灯,永世不许熄灭。”
那光,虽然微弱,却穿透了草原的黑夜有粘钢绞线,照亮了那条通往长安的、遥远的归途。

 15222026333
15222026333